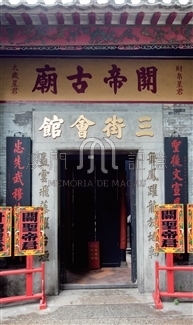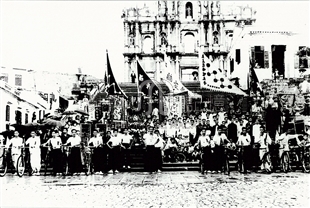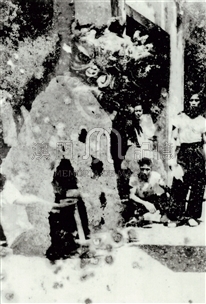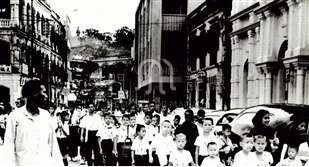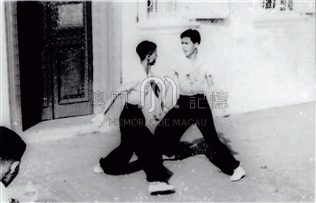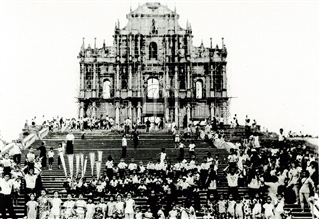“澳門記憶”開站六周年,以“六六無窮‧探索不同”為主題,推出多項周年系列活動,展現“澳門記憶”豐富精彩的資訊,引領大眾探索不一樣或有待了解的澳門。誠邀市民參與,成為建構“澳門記憶”的一份子。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1月31日-1719年2月18日)8月23日,兩廣總督楊琳奏報稱,據西洋人李若瑟說,清朝特使艾若瑟已到達羅馬,並將紅字票遞呈羅馬教皇,羅馬教皇正擬派使節隨艾若瑟來中國覆命,恭請聖安。同時又稱本年五、六、七月,香山澳門回棹夷船在柔佛國、咖喇吧陸續搭回漢人共39名,內有廣東人11名、福建人28名。經查詢,這些人均為未定例以前赴南洋貿易的,還說,在外國貿易的漢人知道禁止南洋貿易後都想回家。康熙皇帝朱批再次告誡兩廣總督楊琳,“西洋來人內,若有各樣學問或行醫者,必著速送至京中”。柔佛,作Johore,即今馬來西亞柔佛地區。謝清高:《海錄》卷中《柔佛國》稱,“在舊柔佛對海,海中別一島嶼也”。咖喇吧,即咖留吧,又作咬留吧,指巴達維亞。《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楊琳奏報續到西洋船數據聞紅票已傳到教化王等情摺》,第114—115頁。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2月11日─1775年1月30日)8月23日,新主教佩德羅薩•吉馬良斯乘坐“西望洋聖母”號從里斯本到達澳門,9月4日就職。佩德羅薩•吉馬良斯主教到任後將南懷仁主教早已接收之北京主教教區管理權收歸己有,以便確認所有葡萄牙籍耶穌會士之職務,遭到以晁俊秀(François Bourgeois)為首的法國耶穌會士的反對,吉馬良斯主教遂命中國副省最後的省會長高慎思(José de Espinha) 神父為其代表人兼北京教區副主教,隨即與教廷傳信部任命的教區副主教約瑟夫•泰雷茲(Joseph de Ste-Thérèse)之管轄權發生衝突,在京傳教士遂分為兩派,葡萄牙人擁護吉馬良斯,法國人和傳信部人員擁護南京主教南懷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167; 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da Marítirna de Macau no Século ⅩⅧ, p. 46;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991頁。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8月23日,美國人乘坐當時世界上航速最快的船隻之一“中國皇后(Empress of China)”號於澳門氹仔泊地5. 5英尋水深的地方,用最好的首錨拋錨,澳門城就在西北3英里外。“中國皇后”號鳴炮七響向澳門致意。澳門炮台也鳴炮致意。大班山茂召(Major Samuel Shaw) 先生在事務長約翰‧斯威弗特先生(John White Swift)的陪同下,光榮地在澳門海域升起首面美國國旗。這是第一艘來華也是第一艘來澳門的美國商船。24日早上,法國領事帶著幾位來自澳門的先生前來拜訪,他們離開的時候,“中國皇后”號鳴放九響禮炮致意。法國領事館邀請“中國皇后”號大班山茂召、船長約翰 ‧格林(John Green)先生及湯瑪斯‧蘭德爾(Thomas Randall)先生等人上岸,到澳門玩了一天,準備去拜訪澳門總督,但總督不在,就在法國領事官邸用膳,出席者還有法國官員和瑞典領事、奧地利大班等。晚上,他們分別在法國領事官邸和瑞典領事官邸住宿。《安森航海記》(Anson's Voyage)的作者說:“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位於珠江口的一座小島上。 它曾經非常富裕和繁華,而且能夠抵禦鄰近省份總督的勢力;但是現在它已經衰落了,境況大不如前,因為雖然由葡萄牙統治,但是它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中國生存,這裡的總督雖然由葡萄牙國王任命,但是必須依賴中國人,只要中國人高興,他們可以把這裡的人餓死,把葡萄牙人趕出去。這使得澳門總督不得不謹慎行事,小心避免觸怒中國人。澳門環境宜人, 在廣州貿易的歐洲商人在這裡安居樂業。一旦船離開廣州,代理人跟中國人把賬算清楚之後,他們便回到澳門居住,直到下一季的貨船抵達。在我們抵達前幾天,當地的荷蘭人、丹麥人和英國人都到廣州去了。”26日,“中國皇后”號離開澳門,朝廣州進發。史密斯(Smith, Philip Chadwick Foster):《中國皇后號》,第162—171頁。關於“中國皇后”號抵達澳門的時間,《山茂召日記》、《美國人在東亞》為8月23日,而《約翰‧格林日記》及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均為8月24日。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8月23日,法國遣使會派遣羅廣祥(Nicolas Joseph Raux)、吉德明 (Jean Joseph Ghislain)神父及巴茂正(Carles Paris)修士抵達澳門海面,但為了避免澳門葡萄牙人的干擾,不敢下船,遂前往廣州,9月1日抵達。羅廣祥,時年31歲,天文學家,並擔任法國遣使會中國教區的會長;吉德明32歲,也是天文學家;巴茂正44歲,為機械師、鐘錶匠。1785年2月7日,他們與另一位鐘錶匠聖約翰佈道會士高臨淵應召離開廣州赴北京,這批遣使會士住進北堂。樊國陰:《遣使會士在華傳教史》,第119頁;《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 第1冊《兩廣總督舒常奏請護送西洋人羅廣祥入京效力摺》,第334頁;方立中(J. Van Den Brandt):《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52—553頁。
光緒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7月,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奉命代表清政府到澳門商辦洋藥稅厘並征事宜。這對葡萄牙來說,以同中國合作的形式對澳門附近走私鴉片徵收稅厘,換取一項中國政府承認葡萄牙佔據澳門的條約,無疑是改變澳門法律地位的一個幹載難逢的機會,甚至是唯一機會。23日,赫德抵達澳門,即與澳督羅沙進行會商,雙方很快達成初步一致。又經過半個多月的討價還價與磋商,於8月10日,赫德與羅沙商訂並簽押了《擬議條約》4款和《續訂洋藥專條》l6條。其主要內容為“中國允准葡萄牙永據統治該半島及其屬地”,“葡萄牙協助中國制定徵收中國洋藥稅辦法”,“中國罪犯逃匿澳門及其屬地,一經中國政府提出引渡,即緝拿逮捕”,“中國允准葡萄牙佔據、使用並管理先前曾有葡人居住之對面山,以及對面山附近之馬騮洲二島。如葡萄牙決定停止執行本洋藥專條,其對前述各島之佔據、使用、管理即告結束”。至此,葡萄牙通過這個《擬定條約》,實現了多年來同中國立約的願望,改變了以往葡萄牙在中外關係中的不利地位。8月23日,羅沙離澳後,於10月底到倫敦與金登幹見面。但此時清政府認為,葡萄牙開價太高,而且反對讓葡人佔據對面山。最後,清廷在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強烈反對下,堅定了不撤走澳門附近常關厘卡及不允許葡萄牙人佔領對面山的決心。陳霞飛:《中國海關密檔》第4卷,第431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總稅務司赫德為香港願辦之處澳門亦願照辦事致總理衙門電文》,第204頁。1887年條約的全部中外檔可見薩安東主編、金國平漢語手稿識讀及翻譯的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葡中關係史資料匯編》),第六卷第一部分第638頁及第六卷第二部分第684頁,澳門基金會,葡中關係研究中心,澳門大學,2000年。重要研究有薩安東的O Tratado Impossivel: um exercício de diplomacia luso-chinesa num contexto internacional em mudança(1842—1887), Lisboa,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2006. 《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第3冊卷68,第12、24頁。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8月16-23日,澳門在美少校操場舉行賣物助賑會,以救濟西江災民。署理總督沙‧方濟各在其副官陪同下主持開幕式,慈幼會學校學生樂隊演奏葡萄牙國歌,由常澤基(Chan Che Ki)致開幕詞。意演中有一台粵劇,記者及富家子弟破天荒第一次在澳門演出話劇。8月19日,新總督羅沙達於就職後的第二個晚上攜帶妻女蒞臨意演。由主席陳席儒等迎入會場,環遊一遍,捐款數金而返。意演中有“小電影”助興。僅此一項收入達5000澳門元。會場人眾,時有意外之虞。紅十字會之西醫廖德山及男看護員黎池,與女醫員羅繡雲、林直恩、余美德,看護婦梁科儀,均入場當意務。是會通計集款,為數甚巨。此項應存為水災善後之用,惟是商辦,善後事宜不可不預定規則,以期協力同心,共收善果。澳門紳商二十五日在鏡湖醫院開會,宣佈進支數目,並決定成立“澳門賣物助賑水災會辦理善後所”,以期合理利用善款。此次賣物並捐助之款約得5萬元。《華字日報》1908年8月21日《澳門賣物助賑會展開》、《紅十字會意舉》,1908年10月1日《澳門賑災會善後所規則》。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30—31頁。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光緒三十四年拱北口岸華洋貿易情形論略”,第256頁。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8月11日,共和派刊物《人民回聲報》 (O Echo do Povo)刊行,其副標題為《絕不妥協的共和小報》 (Folheto Republicano Intransigente)。主編為羅德里戈.沙維斯,並集社長、出版人、編輯等職務於一身。該報為贈閱性質的季刊,先在飛南第家族商務印字館印刷,後在市政廳前地17號《自由報》印刷所印刷,主要宣揚共和、獨立、民主及社會主義。至1924年8月23日停刊,共發行5年。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09-110. 按:此《人民回聲報》不同於19世紀在香港發行的同名葡文報紙。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 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 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 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 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更多
尊敬的“澳門記憶”會員,您好!
感謝您長期以來對“澳門記憶”文史網的支持與信任。為持續優化會員服務品質與保障會員權益,本網站將自2025年4月28日起正式實施新版的《服務條款》。敬請各位會員詳閱修訂後之條款,有關內容可於以下查閱:
您已詳細閱讀並同意接受該等《服務條款》修訂內容。
若您對本次更新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感謝您一如既往的支持與信任,“澳門記憶”文史網將持續為您提供更安心、便捷的會員服務。
“澳門記憶”文史網 敬啟
發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使用說明
檢視全站索引
“AND”,為縮小檢索範圍,表示前後搜索項之間的 “交集”;
“OR”, 為擴大檢索範圍,表示前後搜索項之間的 “聯集”;
“NOT”,為排除不相關的檢索範圍 ,“AND NOT”表示第二個搜索項,在檢索範圍將被排除。
已經有澳門記憶帳號了? 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