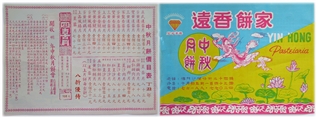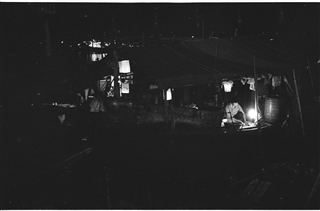為肯定市民積極參與“澳門記憶”文史網各項徵集活動,持續為平台提供豐富的圖片素材,澳門基金會推出“澳門記憶星級榮譽計劃”,透過系統的評分制度及榮譽展示方式,表揚“記憶之友”在記錄澳門、分享故事方面的積極參與。
2026年度星級榮譽榜
賀回歸26載問答遊戲得獎結果出爐!每位得獎者可獲“澳門記憶”手機座連手機掛繩套裝1份 。澳門記憶團隊已透過得獎者註冊會員時登記之流動電話號碼,以短訊形式發送得獎通知,再次感謝會員們的支持和參與!
>>立即查看得獎名單
順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2月19日,南明隆武皇帝頒詔召見畢方濟神父:“臣民強我監國,汝識我已二十年,我誓恢復祖業而竭力為吾民謀幸福。盼我老友速來以備諮詢。我作書召汝已三次,今欲任汝為武職大員,然後任汝為使臣,願汝有以慰我。隆武元年正月初四日。” 畢方濟在澳門逗留一個月後,隨即前往福州。畢氏欲勸隆武信教,以期永生之望。而隆武僅許其在廣州建設教堂一所和居宅一處以及其他傳教特權。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142頁,原法文詔書譯文為隆武元年正月初四。按唐王聿鍵是弘光元年六月十五日在福州即位,當年即“改元隆武”。隆武元年只能從當年六月十五日起算,故無“隆武元年正月初四”說,而應是“隆武二年正月初四”。 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1636,1643 a 1649. Edição, Introdução e Nota de Horacio Peixoto de Araújo,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p. 274;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142頁。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2月19日,澳門土生葡人富商、政壇名人若阿金·巴羅斯在澳門大堂區逝世。巴羅斯1753年生於里斯本縣。先在澳門經商,為第二十號額船“聖安東尼—盧濟塔尼亞(Santo António Lusitania)”號商船船主,主要航行於果阿與澳門之間,曾擔任澳門仁慈堂主席,1801年任葡屬印度領地的兵頭。1809年任澳門議事會市政議員,他還先後於1799、1807、1809、1810、1815、1818及1821年七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其子小若阿金·巴羅斯(José Joaquim de Barros Jr.)1841年11月4日在大堂區去世時,為澳門仁慈堂留下了一大筆遺產。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Vol.1, p.451;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pp.201—202.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1月29日,澳門聖保祿大教堂被一場特大火災燒毀,只剩下現存的前壁。據《中國叢報》載:“大約下午6時半,在澳門聖保祿教堂之上炮台鳴炮,發出火警警報。火警信號很快由其它炮台的大炮聲、教堂敲響的鐘聲和擊鼓回應。當局和軍隊及許多澳門市民立刻就採取了行動。但是,除開那些在教堂附近的原因外,還有一些值得懷疑的、引起教堂失火的原因。——這里的天氣情況是煙霧不能直升,而是被一股西北向的微風吹向東南,整個城市的東部都籠罩在煙霧里。但時間不長,在明火沖上屋頂之前,留下毫無疑問的一點,即火災在何處發生。所有建在教堂左翼,以前由神父居住,最近由葡萄牙軍隊使用的公寓,馬上亦燃燒起來。過了一會,出現了能保存教堂的主體——禮拜堂的一些希望。但是在8時之前,大火燒到了建築物的最高部分及大神壇後部的屋頂。濃煙夾著明火從四周的窗子里沖出來,通過屋頂升起,一派可怕的景象。火苗升得很高,整個市區及內港都能看見。此時正好是(由路易十四世送給教堂的)鐘敲響8時15分。此時,人們努力地檢查了大火漫延的情況。現在,當有明顯的證據顯示大火不會超過教堂建築範圍後,人們似乎希望停止救火工作,並在觀看著火災現場。”2月19日,從該堂中救出的弗蘭西斯科·沙勿略遺骨被轉移至花王堂保存。後來它們又由私人收藏,最後交給了聖若瑟修院收藏。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60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3, No.10, pp.485—486.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1月27日─1847年2月14日)4月19日,海軍上校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抵達澳門。2月13日乘英輪“馬德里(Madrid)”號自里斯本出發。本月18日到達香港,19 日搭乘香港的最後一班蒸汽船到達澳門。21日,亞馬留就任澳門、帝汶、索洛省總督。他是澳門、帝汶獨立於葡印總督管治後的掌管全省治權的第一位總督。據亞馬留帶來的信息,《中國叢報》稱“我們高興的知道,澳門終於成為了各類貨物 的自由港,只有武器、火藥、鴉片除外”。之所以出現如此情況,據澳門主教致里斯本的函件表明,前總督彼亞度對遲遲不採取開港措施負有責任。不久發現,新任澳門總督亞馬留遭到一個在澳門頗有影響的葡萄牙人組成的社團的反對。這個團體不贊成他的反華政策,認為他的反華只是在做黃粱美夢。亞馬留,1803年生於葡萄牙一古老卻世代從戎的貧微士兵家庭。身經百戰,聰明過人,堅毅勇敢。海事及海外部秘書長利馬(Manuel Jorge de Oliveiva Lima)是其靠山,更是海外部長法爾康圈子裡的人。在安哥拉服役時,即與“魔鬼三人幫(法爾康及後來擔任澳督的官也、賈多素)”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參見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82—83頁。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1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No. 4, p. 224;澳門主教馬傑羅於1846年1月21日致海事及海外部部長公函,見海外歷史檔案館,二部,澳門,1846年,轉引自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82頁。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第205頁。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2月19日,雄踞劏狗環(Cacilhas)上面的新碉堡落成。根據命令,取名為瑪麗亞二世堡壘。此即馬蛟炮台,建於馬蛟山上。馬蛟山在東望洋山之北,螺絲山東南,山高47米,是東北海防要地。負責建此炮台者為安東尼奧‧古雅(António de Azevedo e Cunha)將軍。該炮台中央有火藥庫一間,在台北有一塊圓石台,直徑為1. 2米,上置旋轉大炮一尊。炮台還有暗台一座,炮台用吊橋入口,在閘門後有一間圓形大廳,門左側有兩間隱藏室,大廳後面則有回廊。馬蛟炮台建立後,原望廈炮台變得無關緊要,加之年久失修,被命令拆除。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2頁;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35頁。
咸豐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1月22日,熱羅尼莫.馬塔主教諭令,將由法國聖雲仙保祿仁愛女修會管理的聖羅薩孤女院劃歸聖家辣修道院管理。2月19日,將在崗頂奧斯定修道院內辦學的聖羅薩孤女院遷入聖家辣堂繼續開辦,並於本日將新制定的行政、財務管理條例草案遞交政府。馬塔主教還規定從孤女院基金的利潤中徵收1022葡幣,或一次性徵收2000葡幣上繳教區。因為,在遣使會管理孤女院基金的14年(1805—1819)內,基金從4000葡幣增至3萬葡幣;在教區管理的37年(1819—1856)內,基金從3萬葡幣下落至2萬葡幣。根據1856年10月2日法令,葡萄牙國王下令將聖羅薩.利馬收容院和聖家辣修道院合併,而建立一所男子學校。但此法令遭到反對,未能實行。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29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521.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281.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2月19日,望廈鄉紳士生員張耀昌等因澳門政府派員來望廈村“逼索燈費、地租”之事上稟兩廣總督:去年十一月,澳夷又派人入村,如前勒索,並每戶送單一紙,責以繳租遲緩,應行照章苛罰,百端威迫,民不聊生。懇請轉稟督憲,照會該夷禁止收鈔,劃清租界,嚴禁越佔,以別華夷而供正賦。接稟後,兩廣總督張之洞認為“二十年來粵省洋務紛紜,無暇向及澳門,以致彼族暗長潛滋,得步進步,始能私毀防閑[閫],繼則逐漸侵佔,寖而編牌,寖而收稅,寖而屯兵築臺,隱患甚深,關繫甚大,非嚴詰堅持,斷難杜遏後患”。經照會澳督遵守舊章,毋得越境啟釁,勒索租鈔。先是正月時,澳門政府派員來望廈村收租,並進行威逼。望廈村民遂鳴鑼集眾會商抗租,葡人一聞鑼聲,驚惶逃走,此後不再來索租。同時澳門政府還派人到北山、沙尾等處編列門牌,村人鳴鑼將葡人驅走。《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望廈鄉紳張耀昌等為駐澳葡人收鈔勒索請照會劃界禁佔事稟文》,第222頁、《兩廣總督張之洞為葡人佔地勒租事致總理衙門諮呈》,第239頁及《候補知府富純等為遵查澳門地界等情並嚴防葡人侵佔事稟文》,第275頁;厲式金:《香山縣誌續編》卷16《紀事》。
民國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1月,月刊《復興雜誌》 (Renascimento)問世,至1945年9月停刊,主編為弗朗西斯科‧雷戈 (Francisco Palmeira de Carvalho e Rêgo)。該刊編輯陣容強大,許多人都是當時澳門著名人士,包括若瑟‧雷戈 (José Palmeira de Carvalhoe Rêgo)、白樂嘉、謝雷多尼奧‧戈麥斯 (Celedónio Gomes)等。該刊發表了許多極有價值的雜文和學術論文,充分體現了過去400年葡萄牙文化對東方的影響,至今仍是研究澳門史及西方漢學發展史的珍貴資料。至1945年2月19日,《復興雜誌》附屬葡文新聞副刊《復興日報》創刊,至1947年5月28日停刊,社長兼出版人為科斯塔‧馬沙度神父 (João de Costa da Sousa Macedo),主編則由《復興雜誌》主編兼任。該報是二戰後為慶祝“復興”而創辦的,曾同時出版中、英、葡三種文字的版本,是戰後最重要的澳門報章之一。此外,1945年7月1日又創辦了英文版《復興報》,初為週報,後逢週三、周日出版。《復興報》英文版主任及主編為維拉‧弗朗加 (Villa France),總監則為謝雷多尼奧‧戈麥斯。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69-171;林玉鳳:《澳門新聞出版四百年》,載《澳門史新編》第4冊,第1235頁。
因應本澳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宣佈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2月19日,博彩監察協調局表示,翌日(20日)凌晨零時重新開放的博彩娛樂場共有29間,申請延緩開放的則有12間。雖然娛樂場重開,但開放的賭枱在原有數量的30%以下,僅約1,800張,而場內人與人之間亦要保持較遠距離。3月1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創下15年來新低。隨着8月12日、8月26日和9月23日起國內分別恢復珠海居民、廣東居民及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簽注;加上國內經濟環境復蘇,對博彩業的回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隨着本澳新冠肺炎疫情的緩和,考慮到各娛樂場在檢查健康碼、戴口罩、賭客間分隔檔板、保持距離等各項措施等均能嚴格遵守,所以決定放寬防疫措施。2021年3月2日,應變協調中心宣布翌日起,進入娛樂場所無須再出示核酸陰性檢測證明,相信將進一步助力博彩業回暖。
因應本澳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宣佈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2月19日,博彩監察協調局表示,翌日(20日)凌晨零時重新開放的博彩娛樂場共有29間,申請延緩開放的則有12間。雖然娛樂場重開,但開放的賭枱在原有數量的30%以下,僅約1,800張,而場內人與人之間亦要保持較遠距離。3月1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創下15年來新低。隨着8月12日、8月26日和9月23日起國內分別恢復珠海居民、廣東居民及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簽注;加上國內經濟環境復蘇,對博彩業的回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隨着本澳新冠肺炎疫情的緩和,考慮到各娛樂場在檢查健康碼、戴口罩、賭客間分隔檔板、保持距離等各項措施等均能嚴格遵守,所以決定放寬防疫措施。2021年3月2日,應變協調中心宣布翌日起,進入娛樂場所無須再出示核酸陰性檢測證明,相信將進一步助力博彩業回暖。
更多
尊敬的“澳門記憶”會員,您好!
感謝您長期以來對“澳門記憶”文史網的支持與信任。為持續優化會員服務品質與保障會員權益,本網站將自2025年4月28日起正式實施新版的《服務條款》。敬請各位會員詳閱修訂後之條款,有關內容可於以下查閱:
您已詳細閱讀並同意接受該等《服務條款》修訂內容。
若您對本次更新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感謝您一如既往的支持與信任,“澳門記憶”文史網將持續為您提供更安心、便捷的會員服務。
“澳門記憶”文史網 敬啟
發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使用說明
檢視全站索引
“AND”,為縮小檢索範圍,表示前後搜索項之間的 “交集”;
“OR”, 為擴大檢索範圍,表示前後搜索項之間的 “聯集”;
“NOT”,為排除不相關的檢索範圍 ,“AND NOT”表示第二個搜索項,在檢索範圍將被排除。
已經有澳門記憶帳號了? 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