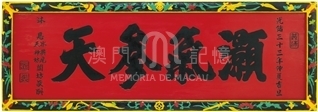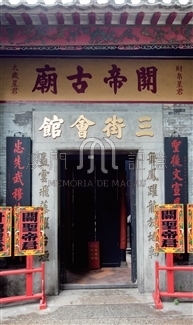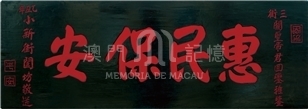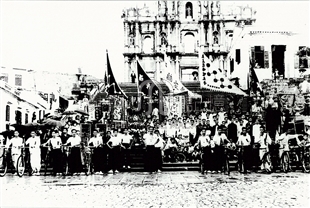“澳门记忆”开站六周年,以“六六无穷‧探索不同”为主题,推出多项周年系列活动,展现“澳门记忆”丰富精彩的资讯,引领大众探索不一样或有待了解的澳门。诚邀市民参与,成为建构“澳门记忆”的一份子。
历史知识大比拼得奖结果出炉!每位得奖者可获 “中西合璧古地图” 澳门通双卡套组。澳门记忆团队已透过得奖者注册会员时登记之流动电话号码,以短讯形式发送得奖通知,再次感谢会员们的支持和参与!
>>立即查看得奖名单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8月5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奏请允许西洋人留住广州称:“现今广西送到西洋人李国善(疑即李若望,João Pereira)一名,湖广送到西洋人方西满(即樊西元,Jean-Simon Bayard)等四名,江西送到西洋人利国安(Giovanni Laureati)等三名,河南送到孟正气一名,及各省续有送到者,今暂在省城天主堂居住,俟其果否情愿回国后,有便船陆续发回,不必限以时日,每岁终造册报部。至于澳门居住之西洋人,各有家室,(为)另一种类,素不出外行教,不在发回之内”。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8《两广总督孔毓珣容西洋人留住广东事》,第34页。
乾隆三年(1738年2月19日-1739年2月7日)8月5日,德国籍耶稣会士鲍友管(Antoine Gogeisl)神父、魏继晋(Florian Bahr)神父和奥地利籍耶稣会士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南怀仁(Godefroid-Xavier de Limbeckhoven)及席伯尔神父乘“圣安娜”船抵达澳门。7日,法国籍耶稣会士嘉类思(Louis du Gad)神父、王致诚(又译王之臣,Jean-Denis Attiret)修士及杨自新(Gilles Thébault)修士抵达澳门。刘松龄、鲍友管能知天文历法,魏继晋能知律吕之学,王致诚善画喜容人物,杨自新能于钟表。10月,内务府将以上五人姓名交与广东督抚,令其派人伴送进京。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26《西洋人徐懋德等奏报新到澳门之刘松龄等有技艺西洋人》,第58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775、778、792、811、820、826页。唯席伯尔为何人?待考。费赖之书及荣振华书均称三位法国教士同抵中国,未言他们至澳门。但《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4卷第287页王致诚的信称他们至澳门。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8月5日,澳门议事会正式向当时已兼任临时代理总督的澳门主教佩德罗萨•吉马良斯征求“允许外国人居住澳门”的意见。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历任葡印总督往往都主张驱逐外国人,认为他们对澳门有害无益。根据当任葡印总督佩德罗•卡马拉(D. José Pedro da Câmarra)的观点,驱赶外国人有三个理由:(一)外国毁坏了澳门的商业,因为他们的存在致使澳门粮食和其他商品价格上涨;(二)澳门居民从外国人在澳门居留中无利可图;(三)外国人的习俗腐化了当地居民。8日,主教兼总督的吉马良斯以经院式的风格分为八点回答议事会的问题。1. 吉马良斯在论述这一问题时特别强调,中国皇帝是澳门的直接主人,澳门向他交纳地租银,我们仅有实际控制权。这块土地不是夺取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居住权并不稳定。我们没有实力,最好忍气吞声,求助于能提供保护者。十几年来,根据中国皇帝的命令,澳门必须接受外国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改变这一决定。2. 我们处在220年前出让的一块贫瘠的土地上,生活相当和谐,出现犯罪时要交给皇帝审判,有的被告在中国被处死,但更多的是实行葡萄牙法律。3. 如果拒不执行命令,我们不能以武力抵御,因为澳门现在有华人近22000人,而所有基督徒,不分老幼男女,皮肤黑白,加起来不足6000人,不堪一击。如果中国皇帝出其不意地让许多中国人闯进澳门,每人扔一只鞋就能将航道堵塞。4. 通过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在中国驻有其代理人或商务员是有利可图的。在船只往来期间,他们可以从容准备下一次装运的货物。这些人不得在广州居住,自然就来到澳门。5. 广州的中国商人手中已经有大量与之贸易的国家的钱,所以他们也愿意让欧洲商务官员在澳门居住。6. 中国政府也愿意保持对欧洲的贸易,他们希望外国人的存在 甚于使澳门摆脱任何压迫,而我们代表中国政府,以我们的法律和司法应付一切,并且可以保存自己。7. 中国人非常明白,澳门人不能取代到广州去的其他欧洲商人,所以不应得罪他们。8. 最后,不应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各公司的商务官交易额为40000两白银,一旦他们离去,澳门不会不感到遗憾。但是,吉马良斯主教对外国人在澳门的影响表示担忧,随着外国商人人数的不断增加,澳门发生了变化。外国商人不断以出血价销货,危及葡商的利益。亚美尼亚商人和英国私商的商品充斥澳门市场,亚美尼亚商人、英国私商和葡商结有盟约,只要他们打着合法葡商的名义掩盖交易, 就可以销售自己的货品,特别是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鸦片,会对澳门的鸦片专卖权构成威胁。他提出驱逐外国人,恢复原来的鸦片垄断,保障澳商的利益。然而,他的建议在当时是行不通的。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4, pp. 204—209.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 Vol. 4, pp. 204—210, pp. 214—215.
四山高拱砲台尊,海气空濛晚角喧。落落老兵扶醉去,斜阳一抹望霞村。望霞村,即望厦村,此为清季丘逢甲当年留居澳门,所作之望厦诗也。其写望厦景色,晚霞一抹,何等诗意!望厦,又有人称之为“旺厦”者,无所取意也。盖昔日在望厦村聚居者,多属闽潮人氏,初只寄居,渐且蕃衍,日久成村。但人本有情,总不能忘怀故乡,因名村曰“望厦”,即取回盼福建、厦门之意也。当年村前之闸门上,有额用草书写成“望厦”二字,以榜村名,所以史地志书等,皆沿称之为望厦焉。兹据:《广东图说》称:“恭都城东南一百二十里内,有小村三十九,曰前山,曰白石,曰北岭,曰澳门,曰龙田,曰龙环,曰望厦,曰潭仔,曰过路环,曰横琴……”《香山县图说》云:“望厦,去城一百三十八里,去寨十八里。”《香山县志》云:“莲花茎山下,有天妃庙,北麓有马交石,稍南为望厦村。”至于澳葡市政厅编印之《澳门市街名册》则称:“望厦村,原日坐落望厦山西南山脚,迨后开辟美副将大马路时,已取销,现已不存。”又曰:“望厦,此名系指本市望厦山之南,及西南地区,该区伸展至雅廉访大马路附近,即大约由罗若翰神父街起,至文第士街止”云。望厦处于濠镜墺北,昔日虽与澳门同在一个半岛上,但各固其圉,各自成乡,澳门称“澳门街”,望厦则称“望厦村”焉。早于明朝,我已派有汛兵一营,常屯望厦驻防。清初,更设县丞分驻望厦村内,以便办理民夷词讼。清道光年间,尚同属中国官吏统治。据祝淮《香山县志》称:“议者以澳门民蕃日众,而距县辽远,移香山县丞于前山寨,改为分防澳门县丞。乾隆八年,以按察潘思渠,总督策楞,议移县丞驻望厦村,设海防军民同知于前山寨,用理猺南澳同知故事……”张甄陶之《澳门图志》又云:“出关闸五里为望厦村,设县丞分驻其他,专理民夷词讼,而统其成于海防军民同知。”《澳门纪略》则云:关闸稍南为望厦村,有县丞新署。”所以昔日望厦村内,有汛地街,即县丞署,及汛兵营所之故址也。自从澳葡开辟马路,已将该汛地街消毁,并为现在之美副将大马路之一部份耳。对于望厦村内之县丞署及汛兵营,又据《新修香山县志》之纪事篇载云:道光二十九年,葡人毁望厦县丞署,侵驻拉塔炮台,县丞迁署前山城内,望厦汛外委退屯白石村三山宫。”杨文骏《查覆澳门新旧界址情形疏》亦云:“查望厦汛旧址,即今之汛地街,原设外委一员,驻紥弹压。道光二十九年,将外委及防兵,迁屯白石三山宫驻防。”自从道光二十九年沈米事件发生后,望厦村内之中国汛兵及县丞,迺移屯白石及前山,故望厦村内之防守工事,概由望厦村民自行组织“望厦乡民知守义团”,负起捍卫社稷责任,在城隍庙址设立团部,士气昂扬,外人虽骄纵,亦不敢稍越雷池半步也。更因村口有石门一度,可以当关固守,村之周围,密种竹树,有如屏幛,村人皆勇敢坚毅,故能保存金瓯,以迄于晚清。其间虽经鸦片战争,义和团之役,八国联军陷京师等等外患时期,难免宵人乘隙觊觎,但望厦村仍能安然独存者,羣众之力也。城隍庙碑记载,两广总督张之洞,曾奏禀清帝,盛赞望厦村人:“望厦村民知守义团,团体独固,深堪嘉尚,不畏时局变迁。戊戌之秋,竟至华洋杂处,余触目时艰,狂澜莫挽,不禁感慨系之耳。”盖至光绪年间,望厦围竹,忽尽开花,翌年全数凋谢。藩离疏落,遂示人以空虚。加以村中难免有一二败类,自甘作奸引线,终致大局不可收拾矣。但村人仍甚倔强,岂肯作顺民,虽然《香山县志续篇》有云:“查望厦村,民房五百余家,系光绪九年占去,添设绿衣馆,马路门牌。”但又有云:“光绪十三年正月,外人逼索望厦等村灯费地租,编列门牌,村人鸣锣号众,外人惧,却走。”所以《中葡外交史》称:“望厦村一带地域,至光绪十六年顷,犹属中国主权,不在澳门范围之内云”。又据“澳门公牍录存”中有光绪十六年香山知县李征庸上两广总督李瀚章禀稿亦称:“关闸以南之望厦村,均系卑职县粮户,从未甘向外人交租,在县控诉有案云”。昔日澳中有一谶语流行云:“竹树开花,夷窥望厦。”竟不幸而言中!自从望厦竹围花后,澳葡迺得入驻望厦。寖且拆闸开路,而石门上之“望厦”匾额,亦被毁灭,只留得村内之城隍庙碑与“望厦村民知守义团”之名共千秋耳。望厦脱瓯后,《百尺楼诗稿》有七言律诗一首咏之云:“偶从野老识村名,泪渍斑斑尚可征。一夜嘶风惊战马;千门浴血饱饥鹰。乡民死士唯知义;胡帅亡元亦薄惩。似为当年留劫火,观音堂上佛前灯。”望厦村情况,老居澳门者,尚未易遗忘。现在宝血蚊香工厂背后,尚有矮屋村道,仍留旧观,俨然小村;美副将大马路中,还有何氏宗祠,沈氏宗祠等在也。攷何氏宗祠,为村中之最古者。往日有一俗谚云:“未有望厦村,先有何家祠”由此可知,何氏族人聚居此间,先于沈、赵、许、黄诸姓,远在望厦建村之前也。望厦村创立自何时,已不可攷。自从闽潮人士移居此间后,生愆日蕃,遂各建宗祠,在此开族,于是蔚然成村矣。攷望厦村昔日之闸门,大约在今之菲利喇大马路北端之尽头处。当民初间,六和自水公司曾在该处,筑一水塔,盖此处井泉清洌,足资饮用,以当时澳中尚未有自来水塘也。殆澳门自来水公司成立发展后,投得专利权,六和水塔迺不得不拆除耳。昔距望厦闸门不远,小坵处有奇石两枚,名公婆石,屼立如人,若夫妇并肩坐,盖天然生成者也。《澳门纪略》尝载称云:“望厦村前二石,每于烟月迷离之际,望若男女比肩立。即之,仍石也。夷人反目于室,出则诣石禳解之,名曰公婆石。”该石经于澳葡开辟马路时凿去,现已不存。至云夫妇反目诣石禳解事,不过传者故神其说耳。望厦村傍以南一带,俱属农田沼泽,阡陌相望。望厦村民在此耕种,原本藉以谋生者。自澳葡入驻村后,便以贱价将田地收买,填作平原。该处当未辟雅廉访马路及未建屋之前,正是一个运动之好场所。一九二六年时,恰逢澳门筑港将竣,曾假此场地举办澳门实业展览会。该会原发起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始行筹办。不料各陈列所建筑将竣之际,忽遇九月一场飓风。所幸损失不大,卒于该年十一月七日开幕。该会地点在望厦场地,面积约二十英亩。内建陈列所六十处,分饰作中葡英荷之建筑型式。展出工商货品五百九十六种,开展时间经三月之久,统计入场者约共二十九万人次,为澳葡繁荣澳门计划之一次杰作。当时曾出巡游会景三天,游龙舞凤,备极热闹。场内更设各种游艺娱乐,曾将望厦原有之古榕水塘,饰作荷兰海岛之风车磨房,俨然水国风光,塘中出赁舢舨,以娱游客,极一时之盛也。在望厦场地,澳葡既于一九二六年举行过一次“澳门实业展览会”后,澳门市面繁荣,不免为之一振,稍现生气。因之澳葡迺于隔一年,即一九二八年,又在原址,再办一次“澳门慈善商业赛会”。是次规模宏大,不亚于前次者,且各间陈列馆,有用砖瓦结构者,至闭幕后,直可成为新辟马路之建筑物焉。攷望厦村自从开辟马路后,已将旧日不少乡闾里巷消毁,盖望厦原有范围,亦颇不小者,试忆当年望厦村内之街道,计有:旗街、公牛街、妈街、汛地街、北便街、田街、牧羊巷、机杼巷、布巷、永安息巷、蛤巷、青砖巷、草蓆巷、土块巷、陈巷、云额巷、草蜢巷、养乐围、杧果围、帽围、见小围、钮里、手折里、树林里、通衢里、田螺里等。又分村为东西两约,虽然是小街陋巷,不下有二三十条,现所存者,寥寥无几耳。当年望厦村内约有户口五百余家,虽属矮屋低簷者多,耕田而食,凿井而饮,亦一安乐之桃源洞也。昔日村中食水用之大井,现尚存在,深湛清冽,称井泉龙王。该井今在保血蚊香工厂后方,该坊居民尚不少以此井水为饮用也。井旁有石碑一方,刻有“井泉龙王”四大字,盖昔日村民迷信,奉以为井神也。碑之两傍,更刻有四言联云:“坎流洊至,井养不穷”斯亦望厦村之遗也。望厦村民,以何、沈、黄、许、赵诸族人氏为最多,故前时各姓皆建立宗祠于村内。现尚存在者,有何氏宗祠、沈氏宗祠、黄氏宗祠等,依然如昔也。惟许氏宗祠则于澳葡开辟马路时,由其族人子孙移迁于关闸外之西瓜埔村中。而赵氏家庙则更早于清朝同治十三年八月间,遭遇一场亘古未有之暴风,全座毁塌,后未建回,现该址遂为葡兵屯营矣。何氏宗祠位于观音古庙不远。根据俗谚所谓:“未有望厦村,先有何家祠”,可知何氏宗祠为望厦村中各氏宗祠之最古者,至少亦逾数百年之久矣。该祠曾经多次重修,始能留存至今。查其最近之一次重修,迺在清末宣统三年,历次修建皆有匾额书明,但惜字迹古旧难辨耳。祠中有颜曰“务本堂”,其两傍联云:“自光州固始以来甫,由化郡新安而入诏。”于此叙明其族迺由北南移,更由闽而迁粤也。闻明宋遗民之何绛,何衡兄弟曾来望厦,驻歇于何氏宗祠。何绛之过澳,汪慵叟有诗咏之曰:“北田高士记陈何,放废佯狂自啸歌,为访遗臣游海外,漫天风雨泣铜驼。”并注云:“何绛字不偕,顺德人。布衣好读书,淹通羣籍。明亡,自放废,与同里陈恭尹为澳门之游。复同渡铜鼓洋,访逃避诸遗臣于海外。晚与兄衡,及恭尹、陶潢、梁琏隐迹北田,称北田五子,见《广东文献》四集《独漉堂集》。”望厦村内昔日之赵家庙,原在观音堂对方右侧,即现在之澳葡兵营处。本属陆氏故园,清初时让与赵氏建祠,其不称宗祠而独称家庙者,盖以赵氏为宋朝宗室,迺宋太宗赵匡义之后裔也,故其门榜以“赵氏家庙”四字。其门联云:“谱分玉牒,系本金华。”二门则有长联云:“溯宋室分封廿七传,世序相承,源远流长,有干有年于兹土;越香山占籍二百载,宗祊肇造,春霜秋露,以似以续古之人。”道光时进士鲍俊,更为撰祖先联云:“迪惟前光,遹追来孝;无忝迺祖,克承厥家。”又据其当年之“赵氏家庙碑记”云:“盖闻宗庙可以观德,祖庙所以本仁。并积德累仁者,无以垂之于后;非敬宗修族者,无以答乎其先;积善者余庆,有志者竟成,吾观于赵氏之作庙,而知之矣。攷赵氏本宋宗室,系出浙江金华浦江县,其先彦方公宦游闽粤,作宰香山,遂占籍焉。传至英玉祖,始卜居于香邑之澳门,世序相承,以孝友传其家,诗书世其业,子若孙,皆彬彬秩秩,有都人士风,识者知其德泽之留遗者,远也。迺家世业儒,素安淡薄,人文蔚起,祠宇阙如。吾友封石无日不悬悬于意中,以艰于财,限于地,又难于经理之得人,故有志而未逮。一日谓其从叔词卿,及其弟彤阶逊夫等曰:吾家自英祖来澳,已历六传,先人虽屡拟建祠,而终无成议,寝庙未成,先灵未妥,为人为子之道,实有示尽,勋蓄此意已三十年于兹矣。语次恻然,族人感其意之诚,无不鼓舞欢欣,捐资襄事。又幸其弟画堂深明河洛,理相阴阳,审向背,得望厦陆氏故园一区,乃与叔弟合力营谋,祠基遂定。从此鸠工庀材,经始于庚子之冬,至辛丑腊月告竣,而家庙以成。夫体祖宗未遂之心,成祖宗未竟之事,非封石仁孝性成,郁积于中,有以咸孚乎宗庙;而族人复能读书明理,深知乎木本水源之义者,何以一德一心,相与有成若是哉!和气积而家道兴,根本立而枝叶茂,吾知斯庙之作,展禴词丞尝之礼,讲冠昏之仪,孝弟之心油然以生,仁让之风勃然而起,将见以道德而发为文章,以文章抒为经济,于以黼黻皇猷,光昭世德,以为本邑生色者,正未有艾也。后之登斯堂者,想先世积累之隆兴,后嗣继述之善,而知百计经营以成此堂构者,其来有自也。予不文,因词卿之请而不获辞,即事之始末纪之,勒诸琐珉,以垂奕禩。戊辰科举人梁尚举顿首拜撰。”溯望厦村赵氏之定居,迺源于明初洪武十九年,赵彦方作宰香山,卒于任内,其后人遂占籍焉。传至明末崇祯十五年,赵英玉始卜居澳门。更历六传而至赵封石,迺建赵氏家庙于望厦,由是子孙世续,书礼传家。在科举时期,代有中式者,如赵元辂及赵允菁,父子先后同中举人。据《香山县志》载称:“赵元辂,望厦人,字任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第十八名举人。”又称:“赵允菁,望厦人,字孔坚,嘉庆六年辛酉科第四名举人,授南雄州始兴县训导。”故昔日在望厦赵氏家庙内,悬有“父子登科”之匾额一个。同治十三年八月大风灾,赵氏家庙被毁后,该匾由其后人保存,现尚悬诸赵家围之赵瑞春堂大屋中也。攷赵元辂,字任臣,号九衢。生于乾隆巳未四年,例授文林郎,覃恩貤赠职郎。以府案首入泮,补廪膳生,乾隆丁酉科中式,广东乡试第十八名举人,著有“观我集”。于乾隆庚子四十五年三月,以会试卒于京师广州会馆,时年四十二岁,迺宋太宗赵匡义之第二十世传孙也。赵允菁,字孔坚,号筠如,赵元辂之长子。生于乾隆戊子卅三年,例授文林郎,覃恩勅授修职郎。嘉庆辛酉科中式,广东乡试第四名举人。道光丙戌乡科会试后,大挑二等,授南雄始兴以教谕衔,管训导事。越二载,李鸿宾制宪谓其足为文士楷模,调委越华监院。邑人士联名请仍留学任,以培士气而励人材。癸巳年升授平州学正,改授京职,签授翰林院典簿,著有《书泽堂文稿》行世。其门人多是当时俊彦,如招子庸,曾望颜等。回忆其卒于道光甲午十四年时,享寿六十七岁,其门人曾望颜太史有联挽之云:“忆马帐追随,道德文章,远大相期,正思义尽恩深,三十年来犹昨日;记羊城叩别,燕台粤海,音书不断,何意星沉月落,七千里外哭停云。”望厦村民,除何、赵、沈、黄、许各族建有宗祠外,村内尚有许多他姓人氏留居,如陈、郑、韦、杨等,皆为邻近乡人流落是间,而在此开族者,数代相传,俨然成为土著矣。昔日科举时代,村中各氏子弟皆以争取功名为闾里光,如赵元辂及赵允菁之父子登科,固在望厦村中一时传为佳话;其他各姓弟子中,亦有奋发而能青一襟者,如陈景华是也。陈景华,字鹿畦,别号无恙,望厦村中子弟也。晚清光绪十四年戊子科,获中第十五名举人。曾任广西贵县知县,秉性刚直,廉洁无私,严明勤政,有干吏之称。因其嫉恶如仇,以故杀当时之巨匪陆亚发,招致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忌,遂逃走暹罗,从事排满革命工作。至辛亥革命后,即任广州市警察厅长,其政绩最烩炙人口者有二:一是捕杀扰乱广州治安之百二友及其他流氓匪类,使地方为之宁静;一是创办广东女子教育院,使广州市内之婢女、妾侍、尼姑、娼妓等都可以得到申诉,脱离虐待而得受教育也。独惜陈执政不久,民国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多逃亡海外,陈恃自己正直无私,卒被龙济光诬杀。时为民国二年九月十六晚之中秋夜,龙假意派人请陈到督府赏月,陈坦然赴约,致被陷害。陈死后,移葬香港咖啡园,其墓碑铭刻道:“强项之令,猛以济宽。冤同三字,狱等覆盆。盖棺定论,毅力维新。哀我民国,丧此良人。”昔望厦村在濠镜墺,孤悬海隅,远离满清统治,故明末志士,前代遗臣,多遁迹斯土,且作寓贤。如方颛恺,屈翁山等,更托身空门,寄居普济禅院。汪兆镛之《澳门杂诗》,有咏方颛恺七言绝句云:“咸陟遗堂莫可寻,宗风衰歇怅而今。山河悟彻微尘耳,但得安居便死心。”盖方颛恺于明朝亡后,削发为僧,誓死不仕,字迹删,著有《咸陟堂诗文集》。其《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诗云:“但得安居便死心,写将人物寄东林。蕃童久住谙华语;婴母初来学鴂音。两岸山光涵海镜;六时钟韵杂风琴。只愁关禁年年密,未得闲身纵步吟。”攷迹删曾于一六三七年丁丑之夏,移锡望厦村之普济禅院。其传见《番禺县志》云:“方颛恺,字趾麐,隆武时补诸生。平靖二王入广州,督学使者檄诸生,不到试者以叛逆论。颛恺誓死不赴,削发为僧,名光鹫,字迹删,后易名成鹫,躬耕罗浮。母殁奔丧,饘粥苫凷,一遵儒礼,葬日负土筑坟,痛哭而后别。俗僧笑之,弗顾也。晚年掩关大通寺。康熙元年壬寅,年八十六卒。著有咸陟堂文集十七卷,诗集十五卷,诗文续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严经直指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道德经直说二卷,注庄子内篇一卷,鼎湖山志八卷。”其遗墨多署迹删,现藏望厦普济禅院者有草书条屏。望厦之寓贤,昔有方颛恺外,还有屈翁山。盖屈翁山亦明末志士也。忽儒忽憎,以隐以逃,与望厦普济禅院之开山祖大汕法师极友善,故尝在康熙二十七年居此。攷屈翁山,粤人,初名绍隆,翁山其字也,又字介子。明诸生,遭乱弃去,礼天然和尚为弟子,释名今种,字一灵,一字骚余。中年返儒服,更名大均,以诗文名世,与陈恭尹,梁佩阑称岭南三大家。著有《翁山诗略》、《翁山诗外》《翁山文外》、《广东新语》、《四书补注》、《皇明四朝成仁录》等书,触犯清廷,多被削版。其《广东新语》内,有《澳门记》,纪述颇详。《翁山诗略》有咏澳门五言律诗六首云:“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功。“南北双环内,诸番尽住楼。蔷薇蛮妇手,茉莉汉人头。香火归天主,钱刀在女流。筑城形势固,全粤有余忧。“路自香山下,莲茎一道长。水高将出舶,风顺欲开洋。鱼眼双轮日,鳅身十里墙,蛮王孤岛里 ,交易首诸香。“礼拜三巴寺,番官是法王。花襔红鬼子,宝鬘白蛮娘。鹦鹉含春思,鲸鲵吐夜光。银钱幺凤买,十字备圆方。“山头铜铳大,海畔铁墙高。一日番商据,千年汉将劳。人惟真白㲲,国是大红毛。来往风帆便,如山踔海涛。“五月飘洋候,辞沙肉米沉。窥船千里镜,定路一盘针。鬼哭三沙惨,鱼飞十里险。夜来咸火满,朵朵上衣襟。”望厦村,虽属穷乡陋巷,但昔日不乏名人奇士,栖隐其间,或以普济禅院作居停,如迹删,今种辈会锡寺中,前文已约言之矣。又闻明末清初之广东爱国诗人陈恭尹,亦尝寄居望厦村焉。故清朝光绪九年进士丁仁长,有五言诗二首云:“本是蛟鼍窟,翻栖猿鹤羣,天方赉幽隐,世不厌风云,画老从仙得,琴清许佛闻,最怜三宿地,海月白纷纷。”“荷阑丰草院,昔我亦停车,欲访天然宇,来寻独漉家,萍蓬似孤屿,天地一枯楂,賸折芳馨赠,春胜菊自花。”盖独漉迺陈恭尹号,言来望厦访其故居也。攷陈恭尹,字元孝,自号独漉子,为明季吾粤三大忠臣陈邦彦之长子。陈邦彦殉难时,恭尹才十七岁,承增城义士湛粹相救,迺得保存忠良遗孤,并以次女妻之。陈恭尹对于清朝,终生不仕,自称罗浮布衣,精书法,工诗文,与当时之屈翁山,及梁佩阑,会称岭南三大家,恭尹且为之冠。晚年隐居北田,又与何绛,何衡,梁琏,陶璜等共称北田五子。壮时,尝与何绛来居望厦,复同渡铜鼓洋,访明末诸遗臣于海外,且与望厦普济院之开山祖师大汕和尚极友善,著有《独漉堂诗文集》。其遗品,有草书条屏,现藏普济禅院中。望厦普济禅院之开山祖大汕和尚,本亦明末遗民,托禅而隐者,故屈翁山、陈独漉等来望厦,与之最友善,盖以其志同道合也。攷大汕和尚,字石濂,号厂翁,自称是当时名僧觉浪杖人道盛之法嗣。尝锡广州长寿寺,又曾至安南为国王求雨而得甘霖,厚获而归。迺大修长寿寺,来望厦营建普济禅院,到清远筑峡山寺,是以普济禅院之祖师堂内有联云:“长寿智灯传普济,峡山明月照莲峰。”中奉大汕自绘法像,作披发头陀状,足见其不肯剃发,不侍清廷也。大汕不泥佛诫,不戒绮语,好谈兵法及当世之务,广交游,工诗善画,百艺无所不能,著有《海外纪事》六卷、《浓梦寻欢》竹枝词卷,《离六堂集》十二卷。易堂九子中曾灿,有《离六堂集序》,其言大汕和尚云:“……和尚为吾乡九江人,少事浮屠,足迹几遍天下。好为诗歌,深得风雅推骚刺之旨。尝与之谈当世之务,娓娓不倦,盖其天文地理兵法象数,以及书画诸子百家之技,无不贯通其源委……今和尚之为人,岂与枯寂浮屠同日而语乎,抑有托而逃者耶?当其狂歌裂眦,淋漓下笔之时,怀抱渊源,空今旷古,此其志岂小哉!然和尚之善藏秒用,又未知其涯矣。”于此可知大汕之抱负,不同凡僧,惜卒招清吏之忌,下其于狱,在破解回籍途中而殒命耳。在穗之商愆鎏太史昔游普济禅院,有咏石濂头陀画像云:“石濂交际徧名流,工画能诗孰与俦,长寿寺门朝市改,低徊小像几春秋。”望厦村自昔与澳门街毗连,交通较便,士大夫来此。以其仍属华人统治,多爱在望厦驻留。且村中有普济禅院,地方轩敞雅洁,骚人画客,每择斯以联坛结社、广交文字因缘,诚望厦村之胜事也。如嘉道时,黄培芳及鲍逸卿等辈,曾在寺中组织诗社焉。攷黄培芳,字子实,一字香石,香山人。迺琼州教授绍统之子,嘉庆甲子科副贡,历任乳源训导,武英殿校录,晋中书,一时硕彦多出其门下。如许乃晋尚书,罗文俊侍郎,林召棠殿撰等,皆属其弟子也。培芳工诗善画,与当时番禺之张维屏,阳春之谭敬昭,合称为粤东三子。道光辛壬间,被委襄治夷务,尝来望厦,与进士鲍俊极友善,结诗社于普济禅院中,一时唱和之声,如漱珠唾玉,澳中文风为之一振。至咸丰丁巳,时巳年登八十,尚重游泮水,学者称之为粤岳先生。著有《易宗》、《浮山小志》、《云泉随扎》、《虎坊杂识》、《缥缃杂录》、《藤阴小记》、《岭海楼诗文钞》、《香石诗话》等,善画山水,法九龙山人。鲍俊,香山场人,字宗垣,号逸卿,道光三年癸未进士翰林院庶士,改刑部主事,候补郎中。工诗词,精书法,善画梅竹,求书者接踵,润笔所入,特构榕塘。其乡有石溪,崖峭瀑奇,幽栖其中,自号石谿生。晚年主讲凤山丰湖书院。著有《榕堂诗钞》、《倚霞阁词钞》。一八四九年澳门之沈米事件,实其主使者也。望厦村,昔日既有诗社,又有画坛。诗人画客,蔚然荟粹于望厦之普济禅院中。文艺之盛,至今犹为人所乐道。法书名画现藏寺中者,皆足为人所珍惜也。如嘉道年间,谢兰生曾来望厦,在普济禅院内之妙香堂,雅辟画坛。一时之骚人画客,如其弟谢观生及孝廉钟启韶等都惠然肯来,羣贤毕集,为望厦增色不少。盖钟启韶于道光时来澳,题有《澳门杂诗》十二首,其中有句云:“思凭谢公笔,图画贮滕。”并自注云:“谢退谷偕行善画。”攷谢兰生,字佩士,号澧浦,又号里甫,别号里道人,南海人也。嘉庆七年成进士,旋选翰林院庶吉士。迭主粤秀,越华、端溪讲席,后为羊城书院掌教。当两广总督阮元重修《广东通志》时,延任总纂。为古文得韩、苏家法,书学颜、褚,书法董、吴,著有“书画题跋”二卷,《常惺惺斋文集》四卷,《诗集》四卷,《北游纪略》二卷,《游罗浮日记》一卷。其弟谢观生,字退谷,号五羊散人,亦以绘事称。与其兄兰生齐名,时称二谢。谢兰生于嘉庆十三年,曾为望厦普济禅院之妙香堂书一匾额,题有“妙香”二字,并序述画坛事。后来该妙香堂,又为岭南画派之高剑父师生辈,作为研究画艺雅集之所。望厦村之文风,以清朝嘉道间为最盛,诗文书画,都有名人骚客为之倡。盖当时之俊彦耆宿,达官贵人等,都常临驻息,或来此办公,或道经暂歇,鞭丝帽影,遗墨留题,已属不鲜;况且村中之文士辈出,如赵元辂父子登科,陈景华中举等,皆为村人所矜道者也。曾望颜太史少时,亦曾随父来此游学,在望厦赵允菁门下受业。后来一举成名,授翰林院编修,还常回乡,道经澳门。咸丰时,尝为望厦重修普济禅院碑记书丹;同治时,又为《澳门创建康真君庙碑志》撰记,其记中有云:“濠镜又名海镜,左有天后宫,右有莲峰庙,带海襟山,华夷杂处,盖邑南之胜境也。余少时,尝从光大夫游学于兹。通籍后,历宦京外,遥别故乡者,三十余年矣。”攷曾望颜,字瞻孔,号卓如,香山人也。嘉庆二十四年举人,道光二年进士,翰林院编修,转御史,迁顺天府尹。累擢陜西巡抚,四川总督,以事劾,罢免。旋被召入都,授内阁待读学士,乞归。其生平居官清介,有惠政。光绪六年,陕西总督左宗棠,奏请于陕西省城建立专祠,并将政绩,宣付史馆立传报可。善画兰石,极秀劲有政,世人咸宝之,见汪兆镛之《岭南画征略》。道光二十四年夏,中西贵要,均到望厦,商订所谓中美互惠商约,即后来之望厦条约是也。当时清廷正在鸦片战争败绩之后,与英国议和,订立南京条约。美国见而垂涎,特派出节使冠兴Caleb Cushing来华,本欲觐见道光皇帝,实行以武力要胁订约,以搀取中国利益。但清廷不欲其来京面谈,特委其皇族亲信耆英,为与美国治商之全权大臣,并即派遣布政使黄恩彤先来澳门望厦,阻止美使北上,故后有在望厦签约之举。望厦条约,迺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五月十八日,即公元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在望厦普济禅院内小花园之石圆台上签定者。清廷方面代表为当时两广总督耆英,两位布政使黄恩彤及潘仕成充任参赞,偕同赵长龄侍御、铜竹樵司马等,办理此事,驻节望厦将旬,公毕然后返穗。美国方面代表为美国特使冠兴,美舰队提督柏架氏竟作威胁式列席,由最初来华传教马礼逊教士之子儒翰马礼逊任通译。此一丧权辱国之条约,虽美其名为中美互惠商约,其实绝不平等互惠,迺在普济禅院签订,有污佛门善旨。现石台石凳仍然存在,商愆鎏探花曾有诗咏之云:“国耻百年湔不尽,犹留石案任摩挲。侵陵外侮通商始,贫困由来血泪多。”攷一八四四年代表清廷来望厦,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之耆英,原迺满清皇室,满洲人,别字介春。道光鸦片战役,英舰扰江宁时,耆英正充杭州将军,统握兵符。惜其素来愚懦惧外,所以败绩求和,曾赴南京与英商订五口通商条约。偷爱偏安之清廷,反以其议和有功,旋授任两广总督。无奈当时广州民众,坚决反对和约,抗止英兵入城,并有三元里之役。耆英遂不得已乞请内召回京,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当其与英签订南京条约时,美国见猎心喜,迺有特派大使来华,要求订约之举。美使本拟亲谒道光皇帝,但清廷避免面议,授命耆英赴澳与之接洽。事前耆英曾发快信三封,并派黄恩彤先来望厦,阻止美使北上。至六月中旬,耆英始抵望厦,由十八日开始酌议,经过两星期磋商,先由美方起草,三天内完成后,稍将部份细节修改,大部依照草约订定,遂于七月三日双方签署。该约共有四本,分用中、英文字缮写,合共三十四款。闻当时约内文字之错桀谬误处,竟达二百余点之多。耆英于签约后,翌日即离望厦返穗。又两月,在黄埔与法使订中法修好条约。后来更与挪威、瑞士等国立约。统观耆英经手所订之条约,无非都是丧权辱国者。至一八五八年,英法两军又入天津,耆英奉召赴天津议和,但以庸绌无能,难于应付英、法要求,无法修改初期经手之条约,迫得惧逃回京。清廷卒以其有亏职责,勅令自尽而死,此即经手签订望厦条约者收场也。商订望厦条约时,清廷耆英曾偕黄恩彤及潘仕成两位参赞到望厦来。黄恩彤,宁阳人,别字石琴,道光初年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当美使来华请订商约未到埗前,先由美国驻粤领事通知广州政府,谓美使将迳由天津直诣北京面帝。广东总督程矞彩未肯答允,只许代奏京师,故受命代表清廷议约之耆英知悉,立即派遣广东布政使黄恩彤赶来望厦,阻止美使北上。此行果然成功,颇获清廷嘉赏,黄恩彤因得赏戴花翎一枝。及耆英来澳,黄恩彤充任参赞,公毕返穗后,翌年擢升巡抚,旋又因事革职。闻咸丰年间,捻军攻山东,恩彤适在籍,献议筑垒掘壕,建炮台以固守,捻军无所得食,致渐穷蹙败退云。潘仕成,广东番禺人,别字德畲,为广州首富,赏布政使衔。因以洋务办盐起家,多与外人往来,故商订望厦条约时,耆英挽其偕来,与黄恩彤同当参赞,襄助订约。公毕,尝同游妈阁,泐石留念。刻云:“甲辰仲夏,随侍宫保耆介春制军,于役澳门。偶偕黄石琴方伯,暨诸君子同游妈阁,题此。番禺潘仕成。”潘仕成雅爱结交文士,尝建海山仙馆于羊城,时作诗酒之会。刊有海山仙馆丛书,海山仙馆法帖等。后因税务事件,卒被查封。望厦条约之美方签署代表人──寇兴(又译顾盛,Cushing, Caleb),本迺美国法律界中人,尝任马萨诸塞州议员。其父曾来中国经商,其兄弟亦在广州致富,原是一个来华贩毒世家。冠兴幼即狡黠;极聪颖,及长,能通多国语言,且能说中国国语,对中国之历史、风俗及贸易习惯等,皆曾致力研究,为一位“中国通”人物。一八四二年时,寇兴在华盛顿国会会议席上,曾极力提出要调查与中国贸易之状况,并拟派遣特别代表团来华,与中国缔结商约。其建议于是年底获得美国国会年会通过,拨助四万元作为出发资金。一八四三年五月,寇兴被委为第一任美国对华外交团团长,暨美国驻华外交特派员与公使全权代表,遂于八月五日,领着四艘美国海军舰队出发来华。启行时,其带有当时美国国务卿韦氏 (Danial Webster)之训令,及美国总统泰莱 (Tyler) 之亲笔致道光皇帝函件及礼品。来华之四艘美舰计为:旗舰米苏里号,拔兰地号,梨酒号,及圣路意士号,当各艘舰只横渡大西洋,至直布罗陀海峡时,米苏里舰不慎失火焚毁。寇兴迺改以拔兰地舰作为座驾舰,遂于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抵达澳门。寇兴来华前,尝夸口必要亲见道光皇帝,使美国取得与英国在华同等利益,孰料被耆英所阻,不得不于七月三日在望厦签订所谓中美互惠商约。迨其返国后,声誉大振,晚年还出任美国之律政司,闻其对驻华之领事裁判权,尚怀叵测云。望厦村后,有莲峰山,为村之屏障;东南尽处为蚧岗,有蟹眼石,普济禅院座其前;莲峰中部垂一脉,石托天然,为燕子巢,故称燕岭,观音古庙筑其下。昔吴应扬太史曾游至此,辟为胜地,尝为观音古庙修撰碑志,且自述云:“予髫龄时,闻澳门望厦乡有莲峰,未之至也。及长,由穗城归里,路经关闸沙,始知为莲茎。茎尽矗起一山,即向所闻之莲峰也。余攀跻而上,见龙势直走,中复垂一脉,石托天然,俗呼为燕子巢,又曰燕岭。”所以望厦,昔人谓其为蚧地,或称之为燕岭。但自澳葡在望厦凿山辟路后,蚧盖为之破碎,燕巢为之倾倒,无复旧观耳。攷吴应扬,号星楼,恭都翠薇人。清同治壬戌举人,戊辰成进士,改刑部主事,升员外郎。辞职归里,主讲丰山书院,教士先气节而后文艺。遇亲友之丧,虽远必吊;遇贫者,更厚赙之。疏财好义,晚年迺家贫,其处之泰然。与两广总督张人骏为同年,张极重之。曾代河南鸡春冈民十六人昭雪冤狱,是以人皆德之。享寿八十余岁而卒。见《香山县志续编‧列传》。望厦村内之庙宇,相传以观音古庙为最古,大约始自明朝中叶。其他如普济禅院,则鼎建于明末天启七年。康真君庙及先锋庙,则大约建自清朝道光年间。而福德祠及武帝庙,迺于清光绪卅三年由龙田迁来者。至于城隍庙,则为光绪卅四年,由观音古庙傍座扩建者也。望厦之东廓,有坟场焉,称“望厦坟场”,或名“新西洋坟场”。昔为村外园地,其北高地旧有基督教坟场,中有廿穴石墓,迺十八世纪时期散葬于澳城墙之外人骨殖,后来迁移丛葬于是者。其下之新西洋坟场,迺因抗战时日人封锁关闸,棺柩不能出闸安葬,故澳葡遂辟此场地以补旧西洋坟场之不足也。抗战后之同胞身死者,仍多埋葬此地,如国画大师高剑父身后亦瘗于斯也。攷高剑父,名仑,番禺圆冈乡人。据其七十岁自述谓:原生于小康之家,诞时适为凶日,家人以其不祥,且属庶出而遭蔑视,几拟弃送婴堂,赖父不忍迺得留养。十一岁,双亲见背,家遂中落。初依兄种田为生,后执役于族叔医馆。叔精医及善绘,暇辄授以绘事,美术兴趣由此启迪。十四岁,返河南兄家,得族兄之介,获免费师侍名画家居古泉门下,虽每日往返十数里至隔山乡就学,弗以为苦也。同门中有伍德彝者藏画甚富,故忍辱叩拜执弟子礼,得其示看,并介绍参观粤中收藏家如潘仕成、吴荣光、张荫垣、孔广陶等之珍藏书画,临摹揣摩,尽窥其秘。后更从法人麦拉氏习西洋画,时因经济困难,迫得出任图画教员。旋积资东渡深造。时年十八,考入日本东京美术学院。在日得识孙中山先生,遂加入同盟会,后被派回粤实行革命工作,凡八年,历次举义及暗杀事,皆躬与其间。迨民国成立,弃功不居,仍旧潜心作画,创办岭南春睡画院,传授弟子,一时称其画为岭南折衷派。一九三零年,周游印度、缅甸、锡兰、不丹、尼泊尔、波斯、埃及等地,艺名日彰。抗战期间来澳,隐居望厦普济禅院,日与弟子等研画于妙香堂。和平后返穗,创办广州高中美术学院。翌年,任广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一九五一年,卒于澳门,时年七十三,葬于望厦坟场。
咸丰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8月5日,澳门土生大富商、大业主埃斯特旺‧卡内罗(Bernardo Estêvão Carneiro)在澳门去世。卡内罗是澳门土生卡内罗家族第二代,1785年11月17日生于葡萄牙赛拉韦扎(Selavisa),何时来东方不详。1819年已在马尼拉从事贸易。1831年以前他已至澳门。1825年他从雅努阿里奥‧阿尔梅达(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手中购买了他的住宅“男爵宫”。埃斯特旺‧卡内罗两次出任澳门议事公局理事官,他在澳门还有一幢大的物业叫“卡内罗花园”,位于叫新雅马路(Estrada da Bela Vista)的地方。卡内罗去世后,“卡内罗花园”卖给英国驻澳门领事克雷威尔利‧奥斯穆德(Cleverly Osmund)作为基督新教徒墓地。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1, pp. 661-662; Manuel Teixeirau,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2, p. 335.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8月5日,澳门番摊承充合同签订,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澳门番摊承充合同。《承充澳门番摊揽头生意章程》内容为中葡文合璧,左右对照。承充的华商为郑耀、刘越犀、钟超三人。条款的主要内容如下:1. 承充番摊合约章程以一年为期。计至1874年9月10日为满期。承充规银15万元,由本年9月11日起。每月上期缴纳规银12500元,七二兑。2. 淮开摊馆26间,不得多开。无论是否开足26间,依然照纳规银。如欲多开须禀明公物会宪。3. 由关闸至妈阁地方所有摊馆生意均归承充人。任由承充人在界内照上款开馆多少。4. 午夜12点闭门。有私开罚银50两。5. 准开打牌馆三间。6. 该承充三人有保险公司50份,每份500两交出作按以为担保规银,另有香港商人担保该三人遵照合同。签名:郑耀、刘越犀、钟超,担保人为和兴李升。通过这一番摊承充合同档案来看,番摊的开设地不包括氹仔,有开设打牌馆以及开设时间的限制情形,这些内容都是以前未曾出现过的。AH/F/422, MIC: A0585. p. 1,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郑观应:《澳门窝匪论》,最早发表在1872年的《申报》中称:“其番摊之馆则已有二百余号也。”由档案可见,仅准26间。很可能郑氏是指赌馆内的番摊赌台数目。
更多
尊敬的“澳门记忆”会员,您好!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澳门记忆”文史网的支持与信任。为持续优化会员服务质量与保障会员权益,本网站将自2025年4月28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的《服务条款》。敬请各位会员详阅修订后之条款,有关内容可于以下查阅:
您已详细阅读并同意接受该等《服务条款》修订内容。
若您对本次更新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感谢您一如既往的支持与信任,“澳门记忆”文史网将持续为您提供更安心、便捷的会员服务。
“澳门记忆”文史网 敬启
发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使用说明
检视全站索引
“AND”,为缩小检索范围,表示前后搜索项之间的 “交集”;
“OR”, 为扩大检索范围,表示前后搜索项之间的 “联集”;
“NOT”,为排除不相关的检索范围 ,“AND NOT”表示第二个搜索项,在检索范围将被排除。
已经有澳门记忆帐号了? 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