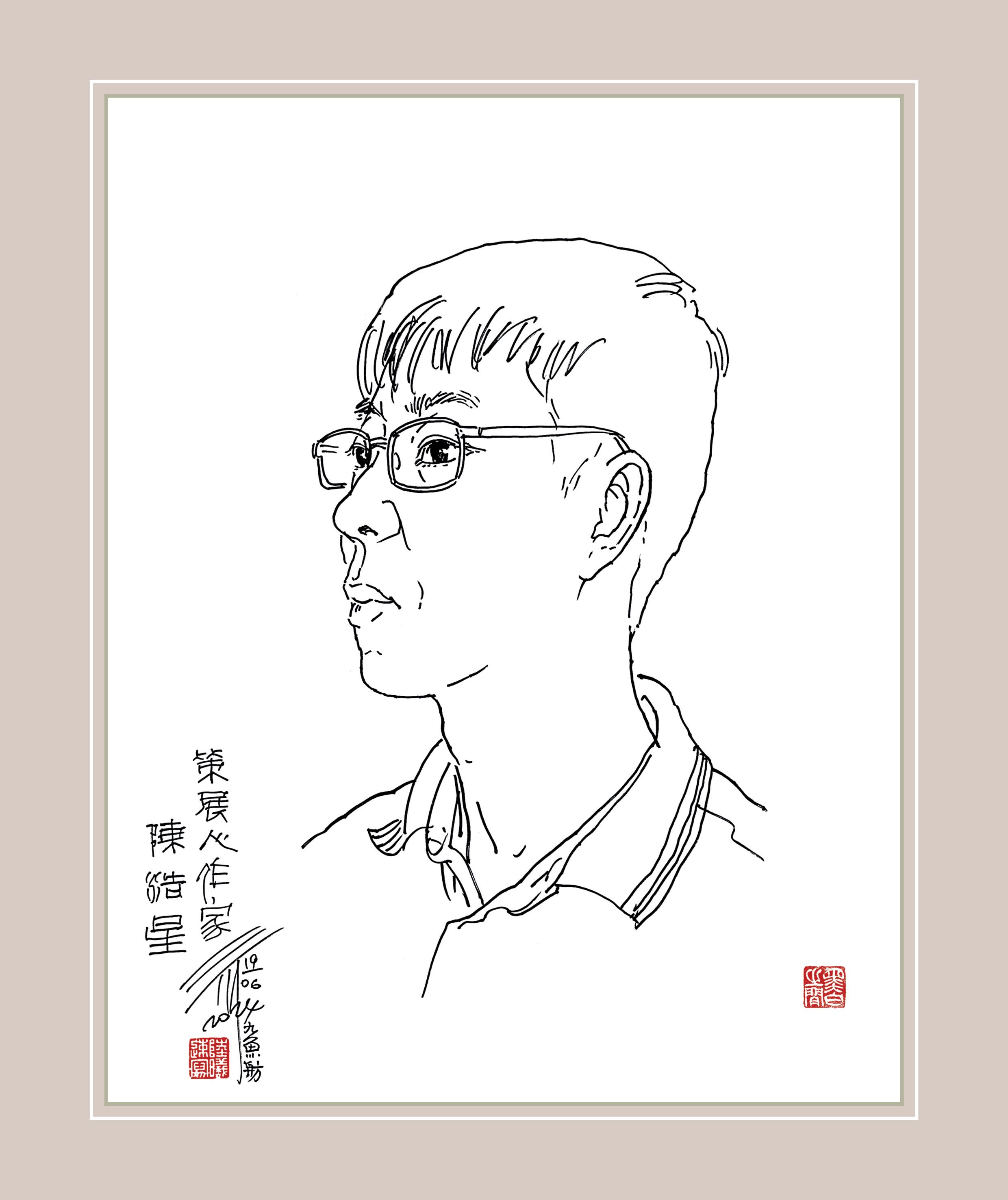
陳浩星肖像
肖像畫作者:陸曦
十月寒露,早晨十點半的檀香山咖啡,艷陽和暖,微風習習,一如陳浩星留給公眾的溫文感覺。
我的文藝觀:文以載道
“於我而言,從政和從事文學、藝術都是一回事。文化的走向關係國家未來,文化是國家民族的根本,也是從政者所必須關心的。”陳浩星要了一杯奶啡,侃侃而談:“我是一個傳統的人,主張文以載道。文藝創作要對社會有正面影響,要介紹、傳播我們的社會文化。”
一九八零年代初,內地開始有作家來珠海和澳門交流。當時,澳門還沒有作家社團,交流活動由當時的文化界前輩組織,直至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澳門筆會成立,成員包括幾乎所有活躍於澳門的作家,其性質相當於內地的作家協會,該會至今仍是澳門特區最主要的作家社團,為澳門文學提供了極其重要的交流平台。身為澳門筆會名譽會長,陳浩星也參與了筆會的籌建工作,對筆會有著深厚的感情。對於即將成立的澳門筆會青年協會,陳浩星亦寄予厚望。“年輕人要有社會擔當。”他說。
傳統藝術之路的起點
陳浩星一九八三年十月進入澳門日報社,編輯過“新園地”“鏡海”“新書刊”“語林”等文藝副刊,但他更廣為人知的,是詩詞、書法及篆刻方面的造詣。
陳浩星的文藝之路,始於家庭教育和師長熏陶。小學時期參加澳門美術協會開辦的繪畫班, 由素描石膏像開始;家庭培養閱讀習慣,內地的連環圖、香港出版的《小朋友畫報》《兒童樂園》雜誌,還有歷史人物傳記等陪伴他成長。騰轉跳躍的線條世界,激發了童年陳浩星對美術世界的濃厚興趣。“其實,我是由(中國)古典文學進入古典藝術的,但我對兩者的興趣又差不多是同時發生。我的體會是,要深入了解中國古典文學,才能對中國傳統藝術的內核有所認知,否則,認知只會停留在視覺藝術的層面。”
買橙,要揀幾個好的,再揀幾個不好的
陳浩星的文藝觀和人生觀,與家庭環境有關。他的父親是海員,活躍於工會,嚮往進步,並給長子改名紅星。陳浩星從父親身上感受到,立身處世,一須熱愛祖國,二須體恤基層。“大姊少時曾隨父上街買橙,父親在攤檔選了幾個好的,又刻意揀了幾個不好的。大姊感到奇怪,詢問原因,父親說,‘儍女,若一味都揀好的,剩下不好的橙,誰會買?攤販怎麼辦?’大姊說,父親這幾句話讓她記一輩子。”
父親的遺物只有自用印一方,書數本,其中一本是艾青的《詩論》。陳浩星說,最令他驚訝的是,父親還留下一本毛筆自書詩稿,寫在一本印務所的拍紙簿,都是五七言近體詩,書法飄逸,寫情抒懷,詩書雙美。父親雖然只念過幾年書,但是有如此修養,令陳浩星感悟自學及力學的重要。
讀書作文萬里路,感恩栽培憶鵬公
除了父親,李鵬翥先生是第二位對陳浩星影響深遠的人。中學剛畢業,他已經認識鵬翥先生。當時,他仰慕的魯迅、郁達夫、郭沫若等文化名人都曾留學日本,他渴望追尋先輩足跡。在日本短暫研習後回澳,蒙李先生栽培,得以進入澳門日報社工作。憶起工作期間,李先生在言語、禮儀、待人接物等方面對自己言傳身教,陳浩星感到無比幸運:“我在報社工作了十四年零十一個月, 差一個月就滿十五年。多年來李先生一直指導我寫作,介紹我接觸社會人士,參與社會事務。即使在我調任博物館之後,依然保持密切聯繫。我很感激他,很懷念他。李先生謙虛好學,我追隨先生三十年,從他身上感悟最深刻的,可以八個字概括──識大體,凡事看大局。這點足以令我受益一生。”今年是李先生逝世十周年,陳浩星以書法參加“二零二四年澳門跨媒體文學大展”:
可奈斯人,心高氣傲;
依然故我,志大才疎。
三十年前,鵬公每誡予勿太書生氣,此見誠是,固我輩所不宜,然鄙意我輩亦不能無書生意氣。此意終不改。寧不聞顧亭林引劉忠肅言:“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乃亭林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予謂讀書有得,期以用世,使心聲文字無補於世,實非予志,故不作可也。士之先器識而後文藝,其理故云然。士有士氣,此予所不敢望,故寧作書生,不作文人。不合時宜,亦自可哂。甲辰重陽,值鵬公謝世十稔,因撰書此聯見意,並懷鵬公之教。
從舊作印證國家發展
性格耿直、被鵬公諄諄告誡“勿太書生氣”的陳浩星熱衷於中華文化,為此寫了不少文章, 但多年來未曾結集出版。澳門回歸後,文化事業蒸蒸日上,文學出版如火如荼,李鵬翥先生及若干好友勸他出書,他都婉謝了,原因是“我的文章沒甚麼特別”。一九九八年,陳浩星轉任公職,籌備澳門藝術博物館開幕,二零零八年起擔任該館館長,期間策劃了數十項中外文物特展, 見證了澳門文化發展和對外交流的歷史點滴,肩負文明互鍳、文化傳播的工作使命。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陳浩星終於首度將二十多年前的作品結集為《夜航隨筆》正編及續編。同時,他也在輯錄《博物文存》和《藝術文存》,“只要對社會有用,我都願意做。我考慮出版文集,只因這些文章是真實、原始的記錄,可供讀者了解澳門文化發展的一些面貌。”他鄭重地說。
最令陳浩星開心的,是從舊作印證國家今日發展。例如他於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澳門日報》發表的新聞特稿《三峽工程舉世矚目》。當時,全國人大常委馬萬祺先生視察長江三峽,他作為記者跟隨報導,一路沿江而下,之後寫下這篇特稿。重看舊文,他“仿佛進入時光隧道”,特別是看到小題為“四川湖北意見不同”這一段:
對於長江開發的次序,是局部治理還是全面治理,是治理主幹或治理支流,目前尚無定論;據知,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周培源據四川、湖北考察得出的結論上書中共中央領導時表示,四川和湖北兩省對三峽工程也有不同意見,四川強調不能放鬆長江上流的開發建設,搞三峽工程不能走上游受損、下游受益的老路。由兩省利益聯繫到國家水利建設的全局,三峽工程備受國人關注是必然的。
“三十多年後,這段文字不但印證了國家建設的偉大成就,也讓我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原理及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感受。”陳浩星感歎道。
對當下很多年輕人工作求安穩、熱衷做公務員的現狀,陳浩星認為年輕人首先應有社會關懷,不建議年輕人一畢業就投考政府工。“年輕人應該要在工作過程中培養判斷力,提高執行力,更重要的是要有服務社會的熱心。對社會要有擔當,對人生有夢想,有理想。當我們批評別人理想主義,還要想到,假如沒有理想,還談甚麼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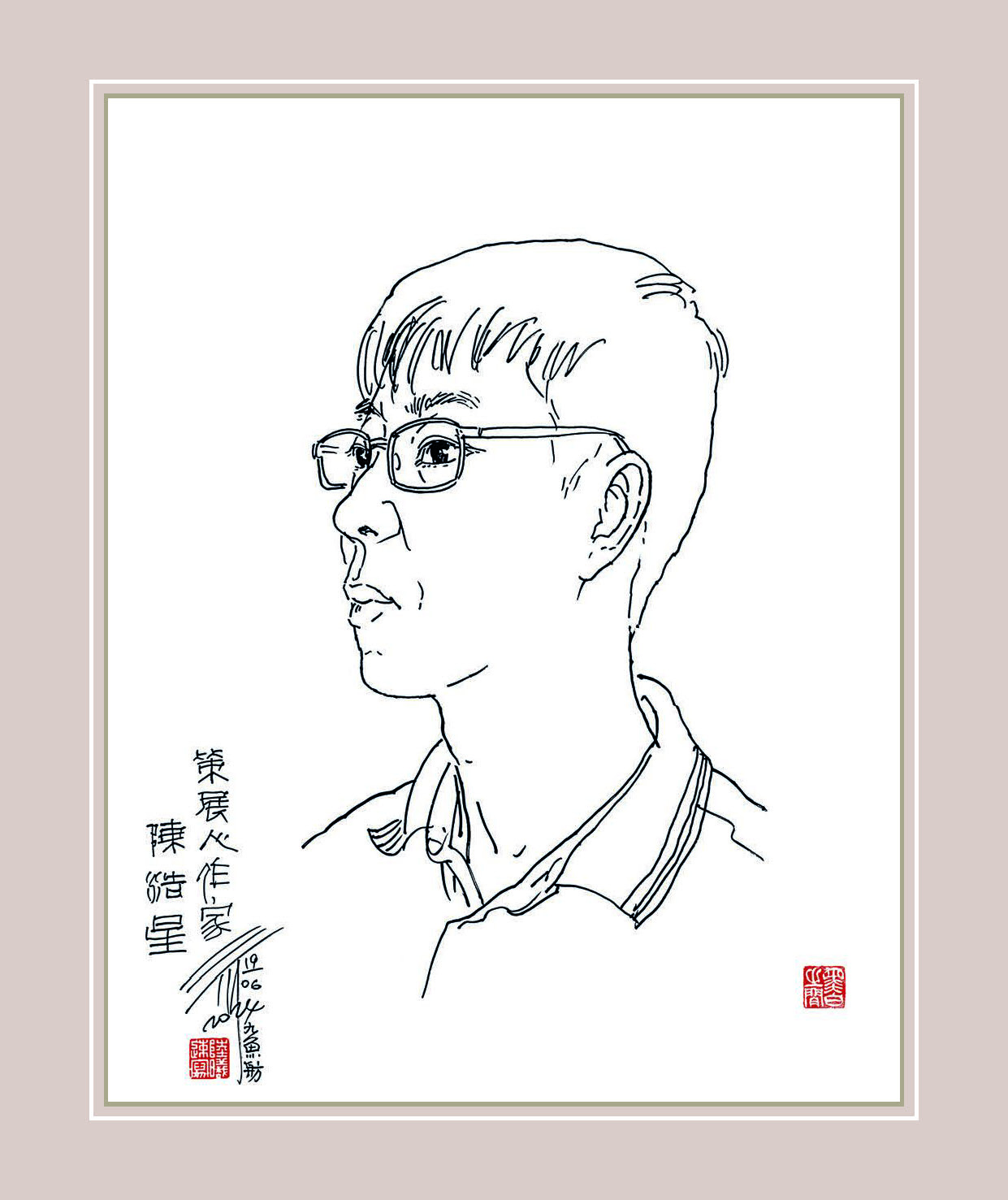









留言
留言( 0 人參與, 0 條留言):期待您提供史料和真實故事,共同填補歷史空白!(150字以內)